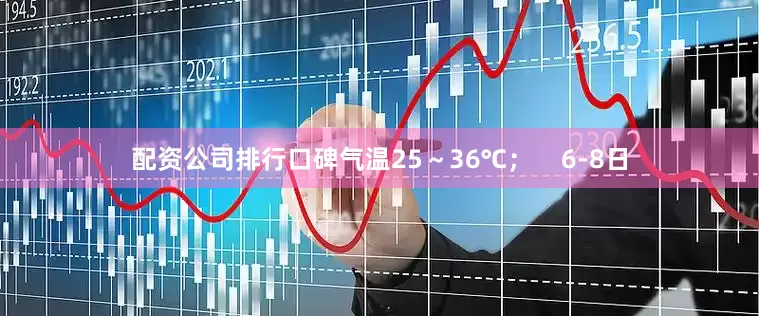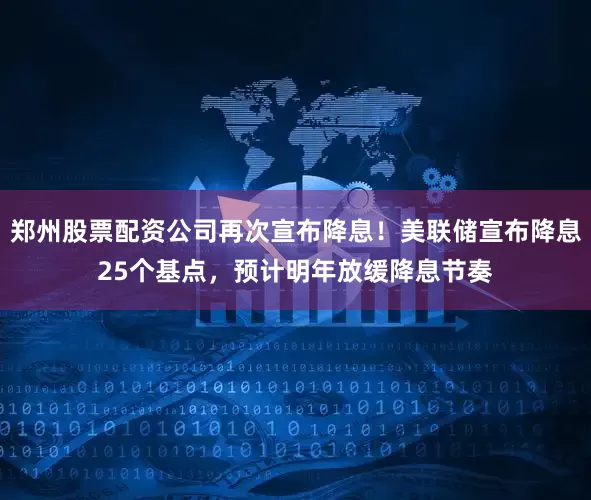“我想离开浪浪山”“我在家乡找灵感”……作为山西文博会的重磅嘉宾,8月21日,开幕第一天,《浪浪山小妖怪》导演、编剧於水带着这部现象级动画作品,亮相山西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发布活动,聊聊“文化打底,科技赋能”的创作理念,谈谈创作动画电影的心路历程,呈现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与科技碰撞。
山西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发布活动现场
不重复、不模仿
“我想离开浪浪山”
“不重复自己,不模仿别人”,这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经典座右铭,也是於水从筹备《浪浪山小妖怪》开始就攥紧的“创作信条”。
展开剩余80%这部动画能火到票房破11亿元(截止发稿),不止因为延续了短片《中国奇谭・小妖怪的夏天》的高人气,更因为它把“打工人”的日常困境,写成了当代人都懂的“自我觉醒”故事:用西游世界观做“壳”,裹着年轻人对“理想与现实””的挣扎——就像那句刷屏的“我想离开浪浪山”,既是动画里小妖的呐喊,也成了无数人想突破现状的“情绪出口”。
为了做出“中国自己的动画风格”,於水没少往“老文化”里钻。他翻出童年记忆里的 “宝藏”:从《中国通史》连环画里学叙事节奏,从《刘继卣闹天宫》工笔画里抠线条韵律,再从戴敦邦《水浒》人物造型里抓“写意感”。这些刻在记忆里的文化符号,被他重新拆解、重组,最终变成了《浪浪山小妖怪》里独一份的视觉语言。
於水导演讲述创作经历
从铁佛寺到北张村
动画里的家乡肌理
更让山西观众觉得“亲切”的,是影片里藏满的“山西元素”。於水在分享里提到,为了让动画更有“在地感”,团队专门从晋北到晋南去采风,把山西古建里的“美”直接“搬进”了银幕。
高平铁佛寺里的二十四诸天像,成了片中四大天王的“灵感原型”;长子崇庆寺的罗汉像,给动画角色注入了“灵动劲儿”;平遥双林寺那尊有“天下第一韦陀”之称的造像,其刚劲的姿态被提炼成了角色动作设计的“核心张力”。甚至连太原的“北张村”这个地名,都被他悄悄植入动画——让观众在看虚拟故事时,能突然触碰到“真实的家乡肌理”。
於水导演讲述电影中的山西元素
当水墨丹青遇上数字引擎
水墨丹青遇数字引擎,技术没抢戏,反而让传统更“活”。“传统文化不是只能‘怀旧’,它需要现代技术来赋能。”在聊到动画制作时,於水特别强调:数字技术从不是二维动画的“对立面”,而是让它“提质增效”的工具。
比如动画里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:火光的暖调、云雾的缥缈,还有国画里特有的 “留白”意境,都是靠数字技术强化了光影层次,才显得更有“氛围感”;而“风吹草地”时那种细腻的动态,是用骨骼动画技术实现的——既保住了二维动画的“手工质感”,又避开了传统手绘“耗时长、产能低”的局限。
文博会现场,於水还专门展示了电影的“线上协作模式”:600多名创作者分散在各地,靠协作平台实时联动——北京动画师画完线稿,立刻同步给上海的水墨渲染团队;山西古建专家不用到现场,通过VR技术就能远程指导场景细节。这种“数字工坊”模式,让二维动画第一次跳出了“手工作坊”的限制,实现了工业化协作。用於水的话说:“科技不只是提效率,更是让二维动画能走得更远。”
於水导演观点分享现场
从银幕到文旅
跨次元的“浪浪山纽带”
“连接现实,助力文旅”,这是於水在分享里反复提到的“意外收获”。最初做这件事,只是源于他“对家乡朴素的爱”,没想到最后竟开辟了一条“二次元连接三次元”的新路径。
他在现场笑着说:“希望大家看完《浪浪山小妖怪》,能像关注《黑神话:悟空》一样,愿意走进山西,去看看铁佛寺的造像、双林寺的韦陀,感受这里的历史和风土人情。”
而《浪浪山小妖怪》的二维动画魅力,恰好成了这条“纽带”的关键:动画里用细腻笔触画出来的山西古建,让观众看完就想“去现实里找原型”;那些透着东方美学的画面,成了吸引年轻群体来山西的“文化钩子”。
於水始终强调“先把作品做好”:只有观众真正喜欢这部动画,它才能产生后续的联动效应。如今看来,他做到了——11亿元票房(截止发稿)背后,是观众对作品的认可;而“从银幕到山西文旅”的联动,也成了中国动画“用文化赋能现实”的典型案例。
於水导演正在接受媒体采访
从1960年《小蝌蚪找妈妈》让“齐白石的画能动起来”,到如今《浪浪山小妖怪》用数字技术让山西古建“活”在动画里,中国二维动画的65年传承中,於水和他的团队正用 “不重复、不模仿”的坚持,让二维动画既守得住传统的“根”,又接得住当代的“审美”,更成了连接文化、科技与文旅的“桥梁”。
(责编:褚嘉琳)
发布于:山西省股票配资工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合法的配资公司因为流通不等同于交易
- 下一篇:郑州配资网站剧中不止瑞秋人设炸裂